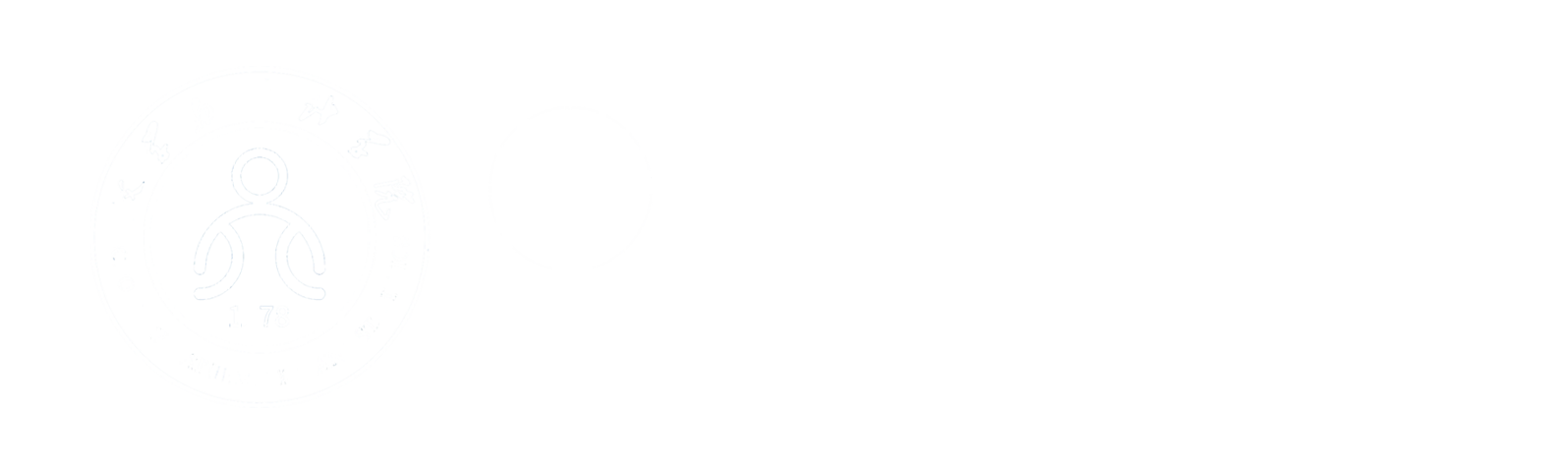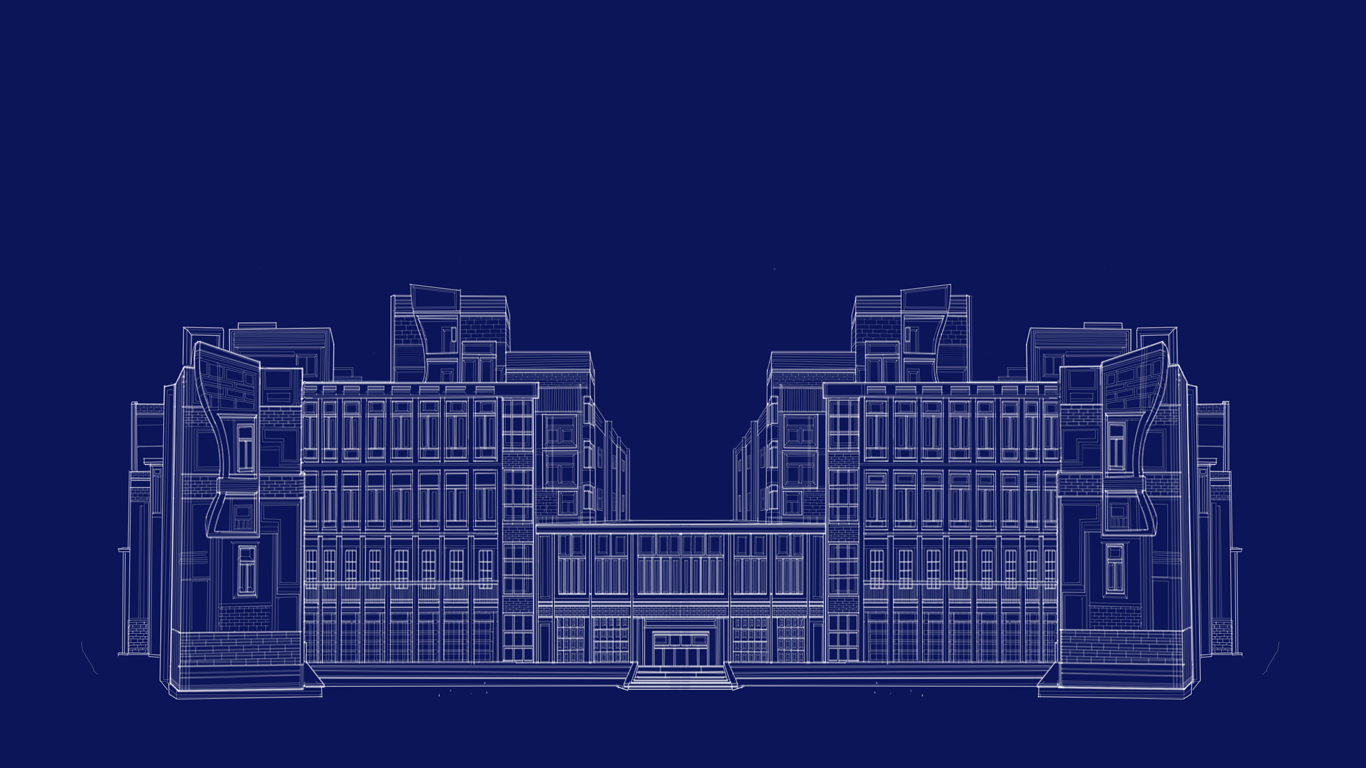万哲先老师的去世使我十分悲痛,我非常感谢六十年来万哲先院士对我的培养和教导。
1962年,万哲先老师为中国科技大学数论和代数专门化十五位大学三年级学生开设《近世代数》课,是我第一次认识万哲先老师。他采用凡·德·瓦尔登《代数学》中译本作教材,以缓慢而精炼的语言和漂亮的板书打动了我,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门讲述抽象代数结构的课程。一年后,他又和华罗庚一起开设《典型群》专业课,并带领代数组八位同学做大学毕业论文,研究各类典型群上的计数定理和在组合设计的应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印度数论统计学者Bose等人推翻了欧拉关于正交拉丁方的猜想,引起组合学界的轰动。这个时期,组合设计被用到工业产品质量控制中,使日本的汽车、造船和电子产品的质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极大提高了组合设计在数学中的地位。万哲先带领学生研究各种典型群上的计数结果,并由此构造出一系列新的组合设计方案。这些结果后来汇集成专著,至今仍被中外学者所引用而成了重要参考文献。我虽然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但是对于万老师捕捉研究新方向的能力和功底,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带领如此众多大学本科生写出系统而深刻的大学毕业论文,非常佩服并受到很多启迪,也促使我对组合学和图论这一数学领域产生很大的兴趣。
1964年我考上研究生,华罗庚老师要我学习代数数论,但只学了八个月。由于1965年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和1966年文革开始,便中断了学习。1973年5月我由太原回到已迁至合肥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暑假期间又来到北京,跟随万哲先老师学习代数编码理论和密码学,十多年后又回到他的身边,和万老师同一个办公室。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数字通信和数字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通信中的信道纠错和先进国家的加密系统均得到重大进步和更新换代。组合数学(包括图论),数论和近世代数学成为信息领域的重要数学工具。万老师从七十年代初带领数学所的年轻人,在文革还未结束时就开始从事代数编码和密码学研究,为我国信息产业和国防事业服务。他率先阅读有关资料,通过消化编写讲稿,然后在讨论班上为我们讲述。不久,在北大、川大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举办短训班,从排列组合和整数分解讲到有限域和移位寄存器序列理论,为我国通信部门和国防单位培训年轻学员,还参加某些研究项目。万哲先老师一直是整个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74年有一次讨论班上,万老师介绍了关于有限域上多项式的一个结果被用到密码设计中,采用了代数数论的知识。这位作者(美国数论学家)突然在数学刊物和国际会议中消失,引发了种种猜测。万老师提议:“我们再组织一个代数数论讨论班吧……学习代数数论,至少能看到漂亮的数学是什么样子!”他当时那种动情的神态,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个讨论班不断扩大,王元老师,北大的聂灵沼和丁石孙先生,以及川大、华东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和辽宁师大的老师也陆续加入。这样,时隔九年之后,在万老师的带领下,我又回到代数数论的学习和研究中,中国代数数论的队伍也重新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他为数学振兴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事情。万老师在北京和东北地区举办过多次代数讲习班,为国内各地高校培养了一大批典型群和李代数等方面的人材。目前国内许多优秀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他培养了许多代数方面的优秀研究生,这些学生后来在国内外取得优异的成绩。其中包括为有关单位培养的博士,后来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院士。他发起在国内举办《有限域及其应用》国际会议,至今已举行了十届。国内外(包括香港地区和台湾)学者会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于凝聚科研力量,提高学术水平和开阔年轻学生的视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万哲先老师生于山东淄博,那里的bwin必赢登录入口有一个“万哲先班”,对优秀的本科生实行特殊的培养方案。万老师多次去进行座谈和指导。后来由于出京不便,有些活动由年轻人代为办理,他都认真听取汇报。2017年他九十大寿时,在北京举办第八届《有限域及其应用》国际会议,他出席开幕式并对协助他工作的年轻人表示感谢,还专门向我问候孙淑玲因骨折住院的病情。
万老师一生写了很多书,有许多是在国内各地讲学的讲义。我十分喜欢阅读万老师的书,并且经常向年轻人推荐,这些书都是他兢兢业业地阅读诸家文献,经过自己的消化,采用清晰而精练的语言重新加工写成,并通过讲解后整理成书。记得他把《设计理论》一书送给我时,微笑并有些得意地说:“我把朱烈的证明写到书里了,你帮我再看看。”我阅读后深为感动,Bose用一篇长文推翻了欧拉关于正交拉丁方的一个猜想,苏州大学的朱烈先生给了一个简化证明,但是要消化这个“简化”证明并且更加精练地写到书中,那是要花很大心血的。
万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我在中学和大学一直学俄语,1978年改革开放后,被选中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在科大参加了半年的英语培训。学习结束后,万老师问我学得怎样,我说考了73分。他只说了四个字:“不怎么样”。有一年我在香港大学做报告,万老师打断我,说我的报告有问题。我回答两次都不过关,头上开始冒汗。最后还是李文卿小声用中文提醒我:“你黑板上一个英文单词写错了。”但是在很多方面,他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晚辈,一直给予切实的帮助和鼓励。他多次为我申请基金项目和报奖热情写推荐信。每次我由合肥来北京,他都问曾肯成的身体如何,了解科大教学和培养学生的情况,使我感到他对中国科技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言语不多,每次和他谈话之后,如能看到他微笑的面孔,便会猜测:大概还是比较满意吧。
我在年轻时能得到万哲先这样数学家先辈的教导和培养,是我一生的幸运。他们在国家饱受战乱,由科举制度到近代化教育的转型时期和动荡年代,为了国家改变面貌艰苦求学。对于民国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风范,追求民主进步和反动势力抗争的独立人格,我从中学时代就充满崇敬之心。2000年我到清华大学工作,其中也有一种心结所致:三十年代清华的算学系,是我心目中神圣的殿堂。我在美国普渡大学访问期间,曾聆听徐贤修先生充满激情地反复讲述华罗庚在清华如何超乎常人的勤奋。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期间,陈省身先生要我们把他的轮椅推到工字厅他求学的教室里,以缓慢的语调回忆清华往事。我也听到过四十年代万哲先老师在清华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他学英语的方式是买一本英文字典,念好一页就撕掉一页......1949年后,他们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付出全部精力和心血。他们淡泊名利,把教书育人作为天职,埋头工作,尽心尽力,热情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愿万哲先老师安息!